一个棒棒的返乡创业记
 作者
作者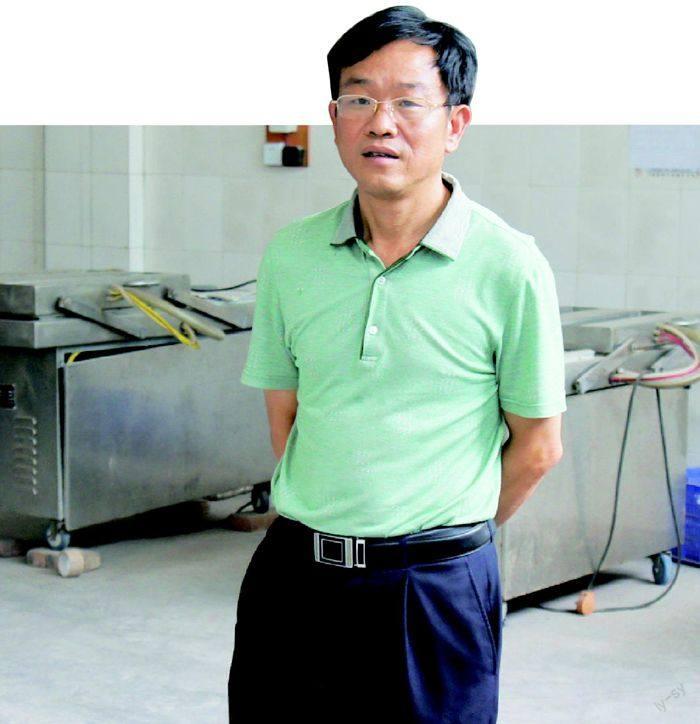
民工返乡潮
在外打拼多年,如今要回乡。城市,还是村庄?曾经外出打工的那个岔路口,又一次横在返乡农民工的面前。
难以想象,站在你面前的一个个披着风霜的农民工,背后都有着讲不完的故事,沿着大街小巷,数着天边寒星。尽管,曾经的村庄,无法种植他们的心愿,但如今乡愁在呼唤他们,自己的家乡等着他们重建,再次成为他们的责任地。
他们已不再是一个“农民”,有的懂技术,有的懂管理,有的卖点子,有的想创业……而家乡也悄悄发生了变化,他们的舞台在哪里?梦想又能否在此发芽?
“项羽说,‘富贵不归家,如衣绣夜行’。我当年曾讨厌家乡生活的穷困,我是有野心的,当初出去打工那天我就想过,总有一天要当个大老板回来,是家乡把我培养成了个小老板,该是我反哺的时候了。”
——熊顺祥
虽说早已过了白露,重庆璧山的温度却超过了39度,宛如三伏,此时正是熊顺祥生意的淡季。贪凉的他起了个大早,去了趟重庆城里头看行情,路过海椒市场时,他看到了几个过去在朝天门一起干活的的棒棒朋友,依旧坐在地上,树个找活干的小牌子,抽烟、谈笑、打牌。而这一次,他没有上前去打招呼。
“我也曾是山城棒棒军”
“不当化学老师了,我要去重庆朝天门当棒棒。”
20多年前,当璧山大兴镇的民办老师熊顺祥做出这个艰难决定时,几乎遭到了全家人的一致反对。在他们眼中,瘦小的熊顺祥是怎么都吃不消码头边上那些苦力活的,在乡下当个老师虽然工资很少,但还是份体面的工作。
“我最早的工作是在重庆江边上‘洗沙’,就是周克华干过的那个活,从早上五六点干到晚上七八点,一天才1块多钱,你根本不能想象那是什么生活。后来当老师以为好点了,但当时教书匠不值钱啊,一个月的工资20块3,照样养不活一大家人。”熊顺祥回忆起当年的生活有点踌躇,任由烟蒂慢慢加长,“当时听人说去朝天门当棒棒每个月‘要赚很多钱’,家里又刚好缺钱盖房子,没有房子,都不好‘耍朋友’,于是我就出去了。”
这一出去,谁想竟是20多年。
最开始,熊顺祥在朝天门帮人搬货,每当有运载着海椒、花椒的大船到岸,棒棒们都会蜂拥到码头边争着“下货”,而他总是奋力冲刺在第一个。但他在搬起第一箱花椒,闻到第一缕麻香味的时候,绝没想过今后为了这些调味料,要耗尽自己一辈子的精力。
“我迷恋花椒的味道,那是一种刺激的味道。每次搬货,我都会大口嗅着那缕缕麻香,奇怪的是,它似乎会让我浑身上下劳累的每个毛孔都得到释放。”熊顺祥对花椒的深入认识,是不久后在重庆菜园坝火车站旁帮着别人卖花椒。“那里的货源供应着整个重庆的麻辣烫,天长日久,我也摸索出一些门道。”
璧山县长期以来是一个农业大县,过去在每年春节后,县里绝大多数青壮年劳力都外出打工,“工字不出头”就是这里广为流传的一句俗语,意思是打工不能打一辈子,下苦力注定这只是吃青春饭的职业。
就是这样的生活,熊顺祥也坚持到自己成为了老板信任的人,带着他到处去进货,“当挣的钱也是少得可怜,老板是不管我们的生存的,我顶不住压力,就自己出来干了”。
十字路口,“一夜白头”
熊顺祥1963年出生,身材瘦小,岁月已经在他那张饱经沧桑的脸上刻下了明显的痕迹,但一双眼睛却闪烁着刚毅自信,一言一行中流露出,这是个精细人。
“我在打工的时候就喜欢观察老板,我发现他们特别能吃苦,胆子很大敢冒风险,而且商业意识很强。对照自己,我觉得这三点都具备,为什么我不能成功?我省吃俭用每月能存一千多块钱,两年下来,就有了两万元的存款。”
熊顺祥有点得意,显然,他是一个很会过日子的人,但能省钱不等于能创业,他在憧憬中开始了在外的漂泊生涯。
他先是南下广西、广东,再一路北上到河南、山东、辽宁,基本上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做过很多种小生意,有时没钱了,运作不顺了,也偶尔打打零工。他不止一次遇到工商、税务甚至消防等部门“方方面面”的“刁难”,效益无法保证。“差不多是个部门就得‘打点’,否则就会以审核、调查的名义让我们停业整顿。”熊顺祥说,根源还是自己是个农民,没有多少社会上的硬关系。
他至今记忆犹新的是坐长途火车的经历:“一般只能买到无座票,一上车就拿出一张报纸,往座位下面一铺,全身尽量缩小,以便可以躺进去,然后就是几十个小时浑浑噩噩。”
此时,他的父母已老,小孩也需要照顾,熊顺祥面临选择,漂泊还是定点。他带着走南闯北积攒下的10多万元,把落脚点放在了家乡,开始从云南等地运花椒回重庆卖。”
熊顺祥第一年拉了两车花椒回去,两万多斤花椒全部由他自己绑上大绳,扛到货车上,睡在花椒堆里两天多颠簸回到璧山,那两天至今被他认为是一种深刻的记忆。结果,运回来一分钱没赚到,还把本钱赔进去了不少。
“当时空有一腔热血,把创业想得太简单。”他说,求爷爷告奶奶似的把前期工作都做完后,终于意识到在商场上人脉关系的重要。“当时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我没有业绩和独自当供货老板的经验,别的商家都不相信、不愿意与我合作。”
一年不行,第二年借钱再来,并且是直接办厂,“说是‘厂’,当时其实还只是个作坊,我看到喜欢吃火锅的人有那么多,觉得做火锅底料生意肯定有赚头。”熊顺祥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说服亲戚,连着自己的,又筹集了一批钱。钱到手后,说干就干,写申请办手续租房子招员工。
依然完败!同时,因为定位不准和市场已有企业排挤问题,导致熊顺祥的生意冷清,只有零星的火锅店打电话要货。
送!一件也亲自送!熊顺祥咬牙拍板,虽然他明白这样只会亏本,但他和他的产品的口碑却在与日俱增,熊顺祥的小厂也在摇晃中慢慢起步。
但人算终究不如天算,一切都看似顺利的时候,熊顺祥下血本在璧山承包的花椒地却完全没长起来,厂子的局面岌岌可危。
厂里的黄大妈至今还记得那一天的情景,几十个跟随熊顺祥一起创业的农民工被召集到厂外的一块坝子上“开会”。坐在一群眼巴巴望着他的人中间,熊顺祥显得心事重重。
“花椒没长起来,厂子要倒了!是重新外出打工,还是再博一次,大家想不想在我这个厂再就业?”一向直言快语的熊老板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吞吞吐吐。
闹哄哄的会场因为这个糟糕的消息而安静下来。人们开始沉默,大口大口地喝茶,或者埋着头抽闷烟,没有一个人表态。而里面抽烟抽得最凶的就是熊顺祥,“我那几天晚上都没睡着觉,坐在门槛上,基本上每晚上3包烟,一夜白头。”熊顺祥直言那是他人生中最艰难的一次抉择。
熊顺祥铤而走险。他开始发动工人,贷款給自己,但当时不止一个人提醒他,“弄不好,你这要成为非法集资。”熊顺祥义无反顾,他很想将自己一手带出来的这批人保住,这批人几乎全是他的亲戚、朋友或者左邻右舍,但这已是向亲友们第N次“伸手”。
对熊顺祥而言,“‘所幸’沿海经济不景气,大家才不愿出远门,加上都是乡亲,最后硬是拼拼凑凑,借到了50多万元,企业重新洗牌,从头再来。”
“东西要真,人要耿直”
大兴镇的乡亲们都爱说,上天注定要考验熊顺祥。一些沿海地区的投机商来到重庆,采用大投入、大资金的模式,也做起了火锅底料生意,并狠狠地赚了一笔。随后,重庆火锅陷入了石蜡造假的信誉危机,虽然最终调查,始作俑者正是“石蜡火锅造假第一人”陈永祥等这批沿海地区来的投资客,但火锅底料的信用危机仍然让熊顺祥这些重庆本地的老板日子不大好过。
“别人吃一把盐巴都没事,但我们多放几颗都咸。”熊顺祥对记者感叹,“他们很多人都是拍拍屁股走人,但吃亏的是我们啊,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信誉又没了,不是说我个人的,是全行业的。”
屋漏偏逢连夜雨,熊顺祥的厂里又接连发生了两个工人偷取火锅底料秘方,投靠了一个“厉害”的竞争对手,让他失去了产品的“杀手锏”。
熊顺祥慨叹,一般来说在农村办企业,没有带头人,很难做成规模,如果是一个人单干,产品的销路就“很成问题”。而一旦成功,跟风的人又特别多,最终结果是“增产不增收”。现在本地的火锅底料厂都非常多,但很多都是开开停停,生命力并不长。那个得到他“秘方”的老板的确小赚了一笔,但听说他儿子今年春节在赌场两个晚上输出去了一个“天文数字”,那个厂在今年也关门大吉了。
“不得不说,农民工出身的我还很缺管理经验,但我的‘秘方’岂是可以随便偷去的,我正准备改良呢。”熊顺祥在慨叹中仍透露出一丝自信。
他又笑了笑,在几个花椒样品袋子里个抓出一小撮,摊开在记者面前:“上中等花椒多为紫红或暗红,每颗花椒旁附有一至二粒花椒,是生意场上的行花‘梅花瓣花椒’,中等花椒,下等花椒色泽多泛黄,掺假花椒则是被人为染色,我们叫‘颜椒’,香味差。”
他眯起眼睛,慢慢地用手工分离出了几份:“不论是山东花椒、汉源花椒、茂汶花椒还是云南花椒。我看一看,摸一摸,闻一闻,大致都能分辨出来,辨认材料这是干好我们这行的基本功,更别说配料熬制了。这些怎么偷?没个三五年是练不成的。”
熊顺祥认为,年轻的时候,一定要多学点东西,找准一个方向,不能因为短期的利益放弃,做久了自然会好起来。他的厂也立下了一条招工规矩:在外地打过工的农民工优先。熊顺祥觉得有过在外面经历的农民工,认知和履历都要丰富些。
而现在他的厂里也有大学生了,是“乡镇上安排过来的,但他们有点浮躁,一来就想干管理。在我的厂谁都必须从最基础的做起,要懂业务流程,这是我打工这么多年的最大体会,不然出去进货和销售时难免被人骗,我就是被骗着慢慢学‘乖’的。但必须抱定一点不变,东西要真实,人要耿直。”
到如今,熊顺祥的货物一天可以发出去上千件了,一年的税收也过了10万元,解决返乡农民工就业五六十人,一个农民工创出来的企业在慢慢壮大。“今后,我要拔些钱出来做公益事业,有几所小学门口那些路都该修了。”熊顺祥说。
“璧山有个做火锅底料的老板多耿直!东西也嘿巴适!”——于是故乡相处流传。
作者 舒炜